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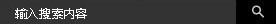

(陈员外家是平城大户,就在这天夜里,他家出了一件轰动的事——半夜闹鬼!
撞到鬼的是一个老婆子,她在路过少爷的房间时,听到屋里有动静。这屋子空了半年多了,一直锁着,怎么会有动静呢?老婆子好奇地扒在门缝向里看。借着昏暗的月光,她看到一个女人在屋子里半弯着腰,脸朝墙壁,沿着墙边走着,姿势很怪异。老婆子见了,脚下发软把门碰得吱呀一响。屋里的女人猛然间转过头来,月光下惨白的脸正对着老婆子,老婆子惨叫一声,昏了过去。
这一下惊动了全家人,几个仆人很快就来到门前,把老婆子救起来。她刚一清醒就大喊:“鬼啊,鬼啊!少奶奶回来了!”仆人们都打了个冷战,左右看看:“别胡说啊!少奶奶怎么可能回来啊!”陈员外也听到了动静,他本已经睡下了,听到喧哗,穿上衣服来到院子里,大家顿时都不出声了。陈员外沉声问:“怎么了,这么闹?”老婆子战战兢兢地说:“老爷,少奶奶回来了。”陈员外一愣,怒道:“胡说什么,少奶奶死了半年多了,你见鬼了吗?”老婆子拼命点头:“是真的啊,我真的看见少奶奶了,就在屋子里啊!”陈员外想了想:“来人,打开房门!”
房门被打开后,大家一拥而入,却发现除了几件落满尘土的家具外,空无一人。老婆子委屈地说:“我是真的看见了,少奶奶就沿着墙在屋里转圈。”深更半夜的,老婆子又言之凿凿,众人都觉得身上一阵寒意。这老婆子在陈家多年,诚实可靠,可如果她说的是真的,屋子没有别的门,片刻时间,人就不见了,难道真是鬼不成?不知谁说了一句:“少奶奶死得不明不白,会不会是冤鬼回门啊?”陈员外脸一沉,呵斥道:“不许胡说,把门锁上。明天白天管家去请法师来。”
第二天法师就被管家请来了,这法师据说在茅山学艺十年,游方到此,本领被传得神乎其神。尽管陈家不想张扬,但法师一路摇铃念咒,还是引来了很多人。看到观者众多,法师十分满意,他走进房间,溜达了一圈说:“你儿媳妇怨气很重,这次回来要报复你们全家。需要大摆香案、大做法事,才能消怨去难。”陈员外正没主意,忽然围观的人群里有人说:“这位法师,可知这女子多大年纪,何时去世,又何来冤死一说?女子家境如何,可有亲人尚在?”众人看发问的人,形貌甚是陌生,四十左右年纪,骨骼清奇,面色红润。身边一个随从,二十左右,容貌清秀,手挑一白布帘,上写着“驱邪解怨”。那法师被责问,怒目而视,但看清此人之后,忽然赔笑着说:“先生,我是混碗饭吃,恕罪恕罪。”说完挤出人群,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大家十分惊奇,这先生笑笑:“我们曾斗过法,他自知不是对手。这起冤孽,不是他能化解得了的。如果主人家有意,我可以试试,如果不灵,分文不取。”陈员外觉得这是个有本事的人,赶紧上前施礼:“敢问先生高姓大名?”先生还礼道:“道号界谛真人。”陈员外吩咐管家备饭,先生摆摆手:“不忙,等我看了屋子再说。清风,在门外守着,不准任何人进来。”
大家在外面等了半个时辰,先生才走出来,疲惫不堪,似乎跟冤鬼较量过一番。陈员外赶紧命人开席。席上,先生说:“你这个儿媳妇是半年前忽然暴病而死的吧,不知当时是什么情况,可否详细告知。我好对症下药。”陈员外叹了口气:“这事颇为蹊跷,还曾惊动过官府。听先生早上所言,已算出了一些?”先生点头:“我掐算过,这女子娘家离此百里左右。半年前暴病身亡,但更多细节,我就算不出来了。”
陈员外说:“先生神通。十年前我刚中举,犬子尚年幼,百里外的孙家庄有一富户,家中公子孙廉与我同科中举。因我俩都无心仕途,很是谈得来。他家有一女孩,比犬子小一岁,因此我俩给两个孩子定下娃娃亲。九年之后,两个孩子都到了婚嫁的年龄,就完婚了。刚把孙姑娘娶到家里时,犬子爱她如掌上明珠,相敬如宾。不想半年后犬子忽然性情大变,流连烟花场所,与儿媳也经常吵闹。儿媳倒是性情温顺,只是默默垂泪。我看不过去,就经常斥责于他。本以为只是小两口间的琐事,谁料一天晚上,竟出了一件蹊跷的惨案。”
先生也不询问,只是举杯沉吟。陈员外继续道:“半年前的一个夜晚,阴天没有月亮,漆黑一片。犬子醉醺醺地回来,不久就从房间里传出了他的叫骂声。我有心去管,又觉得天黑了还去儿子屋里不好。等了一会儿儿子不骂了。半夜时我内人不放心,就让她屋里的老婆子去给儿媳送熬好的酸梅汤,顺便看看小两口和好没有。谁料老婆子连喊带叫地跑了回来。我们到媳妇房间里一看,媳妇脖子上有两道红印,似乎是手掐的淤痕,已经气绝身亡了,而儿子则不见去向。我当时就傻了,想来想去只能报官。
谁知我的亲家因为在家听说女儿女婿不和,特意前来探望。他一进我家门正好看到女儿的尸体,当时就晕过去了。救醒之后我们俩抱头痛哭,真是冤孽啊。知县到现场察看之后,推断是我儿子在与儿媳争执中失手杀人,清醒后畏罪潜逃了。我虽然恨这个不孝子,但毕竟难以割舍,就和知县商量,我愿意多赔银钱,只求莫要下捕文,给犬子一条活路。知县说只要孙家同意,他可以不下文书,但若我儿子潜逃回来,我必须绑子上堂,再审缘由。我就去央求亲家。总算他平素也十分喜爱犬子,虽然痛失爱女,在我央求之下终于还是同意了。只是说自己女儿未犯七出之条,还是我陈家的人,要葬在我家祖坟内。我自然应允。我家坟地是按辈分排好的,各辈都有固定的位置,当下就请几个人来下葬。亲家离去后,再也未上过门,我也羞于再与他往来。知县大人半个月前也告老回乡了。犬子至今未归,谁知又闹起鬼来了,唉……”
先生说:“你儿媳怨气太重,为了清除怨气,我必须带齐法器做法一次。今晚我和清风就住在那间屋里,你告诉仆人不要来干扰我们。”陈员外连连答应。
第二天一早,先生走出了房间,他带着清风离开陈家,吩咐陈员外将房间锁好,并告诉他们,怨气已除,可以放心了。
当天夜里,陈员外被请到县衙,他心里充满疑惑。前任知县半个月前卸任,新任知县还没到任,这时将他请到县衙要干什么呢?正疑惑间,一个身穿官服的人走了进来,陈员外抬头一看,吓了一跳,原来此人穿的正是知县的官服,再一看,更是大惊失色,这知县正是那自称界谛真人的先生!
知县微微一笑:“员外不必惊慌。我就是新来上任的知县,今日刚好赶到。”陈员外尴尬地说:“可大人怎么会……”知县微微一笑:“我素来不信鬼神之事,昨日听说你家作法驱鬼,就前去察看。那法师是个招摇撞骗之徒,在京城行骗时曾被我抓过,我念他只贪财未害人,教训一顿放他走了。他看到我当然害怕,只能跑了。”
陈员外道:“可大人对我家之事,算得神准,又是何故?”知县笑笑:“我虽未正式上任,却已看过了前任知县留下的卷宗,他将你家的案子列为悬案,我自然注意过。”
陈员外还是满腹疑团:“大人今天把小人叫来又是为什么呢?”知县脸色一正,缓缓地说:“今天叫你来,正是要解那夜半鬼回门之谜!”
陈员外赶紧说:“大人只管吩咐。”知县摇头道:“你别说得这么痛快,我说出让你办的事,只怕你就不肯了。”陈员外道:“大人说笑了,小人岂敢。”知县说:“我让你半夜刨坟开棺!”
陈员外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:“这……大人说笑了。小人祖坟乃风水所在,不敢轻动,还望大人开恩。”知县严肃地说:“我朝律法,未得同意私自开坟,乃是偷坟掘墓的大罪,即使是我也不例外。因此你若不肯,我也无法。可我必须告诉你,如我所料不错,你那坟地里埋的绝不是你的儿媳。但愿它是空的,否则……可不要因为一念之差,让你儿子冤沉海底啊!”
知县的话斩钉截铁,陈员外沉默半晌,低声说:“大人,您真的有把握?”知县说:“陈员外,那天你问我名字,我骗了你,但我的名字确实也包含在那四个字里面。”陈员外眼睛一亮:“莫非您是……可您怎么会当知县呢?”知县苦笑:“官场浮沉也是寻常。”陈员外鞠了个躬:“有您的话,别说开儿媳的坟,就是开父亲的坟,我也信您。”
一行人来到陈家祖坟,找准位置,点起火把开始挖坟。荒郊野外,阴风阵阵,棺木露出来的一刻,大家都紧张万分。知县看了一下:“开棺!”
棺盖嘎巴一声被撬开了,随着棺盖抬起,众人一声惊呼,陈员外顿时晕倒在地。那棺木里的尸首虽然已经腐烂,却很容易看出是个男子,陈员外一眼认出那正是自己的爱子!
陈员外泣不成声:“大人,大人要为我做主啊。我的儿子怎么会……我明明亲眼看见儿媳下葬的……”知县心情沉重地挥挥手:“果然不出我所料,你先回去吧,三天之内,当有分晓。”
平成县令迟迟不到,百姓们每天路过紧闭大门的县衙都觉得挺别扭。不过陈家的事倒是挺热闹的,听院里的丫鬟说,那先生说冤鬼回门,必是有什么未了之事,或是回来找什么东西的,因此只要搜遍全屋,找到那件东西,烧化了给冤鬼就行了。为此从即日起正式封屋三日,在大门前焚香祷告,超度亡魂,三日之后,全家动手,搜遍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找出可疑之物烧给冤魂以绝其念。
第二天夜里,暴雨如注。那间屋子里黑漆漆的,锁着的门被风吹得直摇晃。就在这时,屋子里的一块地板忽然掀了起来,在风雨声的掩盖下听不到任何声响,然后一个人从里面钻了出来,他微一停顿,立刻到墙边的箱子里开始翻找。就在这时,一个黑影忽然从角落里窜出来,把那人扑倒在地,随即掏出火折子晃亮了。门外顿时传来脚步声,然后门被打开了,知县和陈员外带着几个家丁出现在门前。化名清风的捕头对知县说:“大人神机妙算,果然有人来了!”
第二天,在大堂上百姓们终于见到了新来的知县老爷,大家惊讶地发现,原来就是那位界谛真人。更让大家惊讶的是,知县老爷宣布要重审陈家儿媳暴死一案。
知县先让人将昨晚所擒之人带到堂上。那人上堂,大家又是一阵喧哗,原来这人大家认识,他是一年前来到平城的一个郎中,就住在陈家大院的隔壁,开了个医馆,平日里悬壶济世,虽不能说妙手回春,却也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。可半年前这郎中关了医馆,出外访师云游去了。
知县看着这个郎中,面目清秀,身材健壮。知县开口问道:“堂下报上名来。”郎中答道:“游方郎中田涯。”知县问:“你可知罪?”郎中道:“小人知罪。小人夜闯民宅,意图偷窃,小人该死。”知县冷笑道:“你确实该死,却不是因为偷窃。你伙同孙氏杀害陈公子,当然是死罪。”郎中猛然抬头:“大人如此无端指责,小人不服!小人曾在平城行医,大家都知道我的为人,我身为救死扶伤之人,怎会害人性命?”知县一拍惊堂木:“好个利嘴匹夫,你也知自己是救死扶伤之人,却行夺人性命之事,今天我若不让你心服口服,我就不叫狄仁杰!”
此言一出,百姓哗然,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当朝一品的神探狄仁杰。狄仁杰在朝中受人排挤,主动要求到下面来当知县,百姓又怎会知道?田涯一听,顿时脸色惨白,惨笑一声,不再说话,任凭狄仁杰问什么,他都不发一言。
狄仁杰也不勉强:“你深夜入室,不是为了财物,而是为了一张纸吧。”田涯全身一震,抬头看去,狄仁杰手上拿着一张发黄的纸。狄仁杰道:“我第一天进屋察看时,就发现地上积满尘土,因此当晚众人进屋时都留下了脚印。在靠近墙边的地方,我在众人的脚印中发现了一些女人的脚印,而当晚唯一的一个女人就是那个老婆子,她穿的是草鞋,那鞋印却分明是绣鞋。我就知道,那位少奶奶绝不是鬼魂,而她回来,肯定是要找什么东西的。”
“第二天晚上,我借作法为名,查遍整个屋子,首先发现了她忽然不见的秘密。我大唐民宅中,多在屋中备有地窖,或大或小,为避战乱、匪灾而设。那晚员外他们也曾向地窖中看过,却未发现有人,可我在地窖下仔细查看,发现有一处泥土很新,我掏挖之下,露出一个地道。捕头顺着地道钻过去,意外发现隔壁是人去屋空的医馆。”
“接着我在仔细寻找之下,发现了这张纸。我知道你一定回来找过不止一次了,但一直都没找到,因为你太专注于那些家具了。因此孙氏才会回来自己找,她确实比你更了解她的丈夫,知道到靠墙的一排书柜里去找。可惜她不够走运,被那老婆子撞到了,因此也没有找到。陈少爷把这纸放在了他最钟爱的一本书里,其实如果你们足够留意细节,就会发现,那是一本《论语》,而这页纸就夹在‘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’那一篇里。我看完这张纸,就基本明白他当时的心情了。”
狄仁杰不往下说了,他将那张纸压在桌案上,又拿起另一样东西来:“后来我在你的医馆里发现了同样明显的脚印,我就知道,我必须调查一下这个医馆的主人了。调查之下,我意外得知你居然也是来自百里之外的孙家庄,这就让我想通了另一件事,你和孙氏是怎么认识的。我让人到百里之外的孙家庄调查一下,得知孙氏小时体弱多病,一个医生多次到她家为她诊治。我想,那是你的父亲吧,你应该是在那时候跟随父亲去孙家,认识孙氏的。”
田涯忽然笑了,声音很大:“大人,你说的都对,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孙氏并没有与我合谋,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,你杀了我好了。孙氏早已在千里之外,你找不到她了。”狄仁杰点点头:“你也算条硬汉子,可惜为时已晚。孙氏既已有孕,你又怎会让她离你千里之远?我的人已经在周围村子搜寻,想来也快了。”田涯瞪视着狄仁杰:“你怎么会知道她怀有身孕?”狄仁杰道:“就凭你身上带着的药,昨天抓住你时你身上带着的两味药材,都是配安胎药用的,你已经在四处藏身,哪里还会顾上给人看病,再说你身上有钱,也无需看病挣钱。这药材自然是孙氏用的。”就在此时,一个衙役上堂禀报:“大人,我们找到孙氏时,她已经自缢身亡了。尸身现在外面。”另一衙役随后上堂禀报:“大人,孙氏之父孙廉带到!”
后一个衙役说的话被田涯的狂吼声打断了,他疯了一样往外冲,两个衙役用尽力气才把他按住。狄仁杰叹口气:“你不用急,我让你见她就是,来人,把尸体抬进来。”
孙氏的尸体用白布盖着,田涯扑在她身上痛哭失声。而孙廉一脸悲戚的看着他,并没有上前。狄仁杰道:“孙廉,那地上的可是你的女儿?”孙廉点点头:“正是。”狄仁杰问:“你为何不伤心?”孙廉惨笑道:“半年前她就该死了,半年前我也已经当她死了,现在不过晚了半年而已。”狄仁杰说:“你的爱女之情我能理解,可你既然中过举,当知律法,可知包庇以同案论处吗?”孙廉平静地说:“小老儿一把年纪了,死也无妨,只是愧对陈年兄,无颜见他,如果大人能替我带句话,我感激不尽。请告诉陈年兄,我来世结草衔环,为自己和小女赎罪。”
狄仁杰点点头:“事已至此,不妨把一切都说出来吧。”孙廉道:“小人原本也知道小女和田涯自幼相熟,但总以为只是小孩心性。当初小女也曾闹着不嫁,可自古婚姻皆由父母所定,我和陈年兄有言在先,那陈贤侄也是个知书达理的英俊少年,足以配得小女。女儿出阁后,听说两人相敬如宾,我也就放心了。可谁知半年后的一天晚上,田涯忽然骑马赶回来,上门求见。见到我后只说女儿出事了,让我去救她。我大惊之下追问,他承认他和小女失手杀了陈贤侄。我让他去见官,他苦苦哀求,说他死不足惜,只是我女儿却也要被千刀万剐。我当时心一软,就答应他跟他去救女儿了。他告诉我,到了陈家,不管看到什么,都不要管,只管要求陈家速速安葬小女就是。我不明就里,星夜赶往陈家,却意外发现小女已断气。我伤心之下,心想既然两人都已死,也就不用和陈年兄多说,只按田涯所说的做就是。哪知一个月之后,田涯和小女忽然半夜到家里,和我见了一面后说要远走高飞。我才知道女儿未死,但其中缘由,却并不清楚。”
狄仁杰转向田涯:“田涯,剩下的事,是你来说呢,还是我来帮你说?”田涯喃喃道:“珠儿死了,我也不想活了。你想知道什么,我告诉你就是。”狄仁杰道:“如果我所料不错,你是在孙氏嫁过来后,从孙家庄过来的。你买下了陈家隔壁的房子开了医馆,然后每天夜里在屋里的地窖里挖土,直到挖通了与陈家一墙之隔的地窖。自此趁陈公子外出会友时与孙氏幽会,可是有一次不巧被陈公子撞见了,我说的对吗?” 田涯点头:“对。陈公子十分愤怒,但他对珠儿甚是宠爱,怕事情张扬出去,父亲会让他休妻。因此他让我们写下保证,发誓以后决不再来往。我和珠儿都在上面按了手印。他将我赶走了,但并未发现地道,只以为我是翻墙而入的,因此第二天让仆人在墙头上插了铁针。本来此事到此为止,我也心灰意冷,决定卖掉医馆回家,但心里却难以放下。后来我听说陈公子开始对珠儿打骂,心知他是难以释怀,不禁十分担心。有一天,我从地道钻过去,想带珠儿远走高飞,珠儿不敢,正在争执之际,陈公子回来了。他想杀了我,我怕他惊动陈家的人,失手打破了他的头,他就死了。”
狄仁杰说:“接下来你将孙公子从地道中拖回自己的医馆,然后星夜回孙家找孙廉,这些我都已知道。可为何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孙氏死了?”
田涯笑笑:“大人,我家世代行医,有一祖传秘方,从未给过外人。此药吃下去之后,人会假死,有如冬天的蛇虫一样,全身冰冷,呼吸心跳都接近停止。不是极其仔细地验看,都会以为已经死亡了。而且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棺材里,只要在棺材上钻两个孔,就不会轻易闷死。当然这样也是很危险的,但当时我们决定拼死一搏。天可怜见,当我晚上将她救出来时,她还没闷死,我给她吃了解药,将陈公子的尸体埋在里面,然后就离开了平城。”
狄仁杰点头道:“这就是了。但那一纸文书却始终是你们的心病,本来你们想活一天算一天,可孙氏有孕,却让你们做长远打算了。你们知道,一旦那张纸被发现之后,你们的孩子不会有将来,对吗?”
田涯惨笑:“我终于知道您的厉害了。大人,我能提个请求吗?我知道自己十恶不赦,可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和珠儿葬在一起,不管怎么说,我也是为了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低,慢慢伏倒在尸体的身上。一个衙役上前探探他的鼻息,摇摇头,忽然问:“这会不会是假的?”
狄仁杰叹息一声:“他心已死,何必再演戏。他既有让人假死的药,也必有让人真死的药。随他去吧,由孙廉带走,葬在一处,即使是陈家儿媳,那孙氏也不必葬在陈家坟地内。孙廉,你葬完他们之后,回来受刑吧。”
孙廉深深叩首:“多谢大人恩德,孙廉来世再报。”
捕头轻声问狄仁杰:“大人,要不要派人跟着他?”狄仁杰点点头:“他不会再回来了,等他死后,让当地官府葬了他吧。他家没什么人了,家产一半给苦主陈家,一半充公,做些善事,也算替他赎罪了。说到底,他罪虽重,却也不过是为人父母罢了。”
狄仁杰退堂之后,朝廷圣旨已在后堂,他跪地接旨。圣旨语焉不详,只说宫内出事,太子有谋反嫌疑,武皇命他回宫审案。狄仁杰愣了一下,接过圣旨,仰天长叹:天下父母者,何以如此不同,有人为子女甘愿一死,有人为权位骨肉相残。武皇啊武皇,你可也是太子的亲生母亲啊!

|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