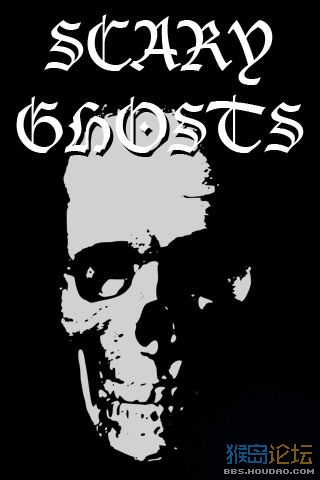
好似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,夢里的我滑過一條黝黑深遠的甬道,然后掉跌下虛無的空間。我驚醒過來,一頭的冷汗。看了看窗外,已是漆黑一片。
打開電腦連接上線——這就是標準的網蟲生活,就算半夜起來上個廁所也要順帶去網上瞅瞅。
信箱里有幾封郵件,兩封來自那個叫云煙的MM,問我怎么幾天沒來上網。我對著電腦呵呵一笑:這個MM大概對我動了心了,我不過睡了一覺么?就說幾天,夸張!
登錄了QQ,意外地看到她仍在線,不等我站穩,她的話就潮水般涌過來了:“好久不見!去哪了?出差了?還是戒網?亦或受了什么刺激了?”
我嘻皮笑臉地回她:“想我了?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呀?”
她不客氣地罵:“是呀,報紙上說有個男子撞車撞成了植物人,現在還躺在醫院,我以為那個就是你呢!”
“你這MM真是黑心腸!不過還真叫你這烏鴉嘴給說中了,我今天還真撞了車。”
“傷哪了?嚴重么?怎么那么不小心呀你?”
傷哪了?我看了看自己,“好象也沒傷哪,就是撞車后總覺得腦筋有些不清醒,好象失憶了似的,走路也頭重腳輕輕飄飄的。”
這不,撞車時我記得好象頭痛得利害,模糊中好象他們把我送進了醫院,后來怎么治療我又怎么回的家,我都想不起來了,而且現在好象什么事都沒有。
“孤身一人在外,凡事要小心點。”
看著她快速的回話,心有隱約的快樂,也有絲絲感動:知道她是真的關心,可是還是捉弄她:“呵呵,好兆頭,開始知道關心我了。”“你真是——非要逼我罵你開心是不是?我是擔心你死了都沒人知道!”“放心,知道你這樣關心我,我就算死了也會纏著你的。”我就愛在網上把她氣得一愣一愣的。
投桃報李,我也關心她一回:“這么晚還不下?明天上班嚇著同事就不好了。”
“今天星期五呀!明天不用上班。你撞車撞糊涂了吧?”
什么?星期五?!不是星期一么?我把鼠標移到右下角,電腦顯示出日期:2001年11月1日。“咦?我是10月26日星期一在上班的路上出的車禍,怎么……”中間丟失的幾天時間我哪去了?又做了些什么?
我有一時的失神,QQ發出的聲音把我拉了回來,云煙在說:“可能你真是太累了吧?不要再玩了,下去睡覺。”
“下去睡覺也行,你要先答應我件事。”
“???”她打了幾個問號過來。
“我要見你,”我想了想,加了幾個字:“以前天天與你聊天,不覺得什么,幾天沒來上網,才發現自己實在掛念你。”自己是在說謊,我連這幾天自己哪去了都回憶不起來,哪來想念她?可是說這話時心里又好象真的很想很想她。
她遲疑了一會,答應了。約好在明晚——哦不,應該是說今晚,現在都已經是凌晨時分了——八點半在“清心咖啡屋”見面。
莫非我撞壞了腦了?下了線我努力回憶了半天,仍不得其解。模模糊糊間又再睡著了。再醒來,一看,壞了,又是天黑,我還約了云煙呢!
連忙起床換衣服,刮胡子,湊近鏡子看,咦?鏡子什么時候壞掉了?竟然照不出我來?一看手表,沒時間了!急急忙忙地往“清心咖啡屋”趕去。站在路旁攔“的士”,那些可惡的司機竟然個個都象沒看到似的理都不理地飛駛過去。坐公共汽車又得兜個大圈,我只好抄小路趕過去。
氣喘吁吁地奔進咖啡屋,大概是跑得太急帶起一陣風,把前面的男子駭得猛地回過頭來,摸了摸后腦勺,對身邊的女子說:“怎么涼嗖嗖的?”
我四下張望尋找云煙,突然在雜亂中聽到——又好象不是聽到,是接受到的一段思維:哪個會是“滄海”呢?
凝神一看,臨窗處有個紅衣少女正瞪著一雙剪水秋瞳盯著門口。云煙!一定是她!我幾乎馬上就斷定下來。
“嗨!云煙!”我走到她面前。
“滄海?”她嚇了一跳,視線卻象找不到焦點似的到處飄,“是你嗎?別玩了,快出來!”立起身來裝得真的似的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的。
我樂了:“想不到你在現實中也這般頑皮!”
“我頑皮?是你頑皮還是我?別躲了!出來吧!”
“我不就在你面前么?誰躲了?”
“再鬧我就生氣了。”
我突然感到有些不對勁:她好象是真沒看到我,否則以她現在的演技她可以去當演員了。
猛然想起這兩天來自己的異樣,想到空無一物的鏡子、視而不見的司機、走在我前面的男子、現在的云煙……有股冷氣由腳底一路攀爬到心里。我被自己的想法驚得呆住了。
“滄海?”云煙試探地叫著。
我繞到她背后,拍拍她的肩。她回頭,大眼睛里滿是驚懼:“誰?!”竟仍看不到我!!!
“對不起!云煙!”我極度驚慌之余,虛弱地拋下句話,返身往門外沖——現在知道自己不是在走,而是在飄了!
我縮在街頭黑暗的一角,一遍遍地問自己:我死了么?我是死了么?怎么變成這樣子了?好象是實在的,又好象是虛無的?
思緒很是混亂,我努力地回憶自己撞車后的一切……醫院?對了,醫院!
我游魂似的趕到醫院,好象有誰在指引著,很直接地來到一個病房里。眼前所見的又把我嚇得魂不護體:病床上分明躺著另一個自己!
恍惚間自己好象是躺在床上的植物人一樣的肉身,又似乎是立在床邊的這個靈魂,可是又好象分出第三個來飄在空中看那兩個“自己”說話。
“嗨!哥們,我回來了。”靈魂滿不在乎地對著肉身說。
肉身恨得咬牙切齒,卻力不從心,無法動彈。只能用細若游絲的聲音惡毒地狠罵:“你還知道回來!若不是我拼命護住僅余的心脈,別人早把我燒了!我看你以后上哪去!”
“你總用這副臭皮囊把我困得死死的,我有機會跑出來還不趁機自由幾天?說實話,要不是沒有你我就沒辦法被這個世俗所接受,也沒有辦法和云煙見面,我還真不想回來。”靈魂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。
“你少廢話!要么進來!要么從此當你的游魂野鬼去!”我的肉身又開始暴跳如雷。
“唉!俗身就是俗身!盡管我不喜歡你限制我的自由,可是沒了你也不行。”靈魂還在那掉兒郎當,驀然空氣中有個威嚴的聲音大喝:“三魂七魄不許再胡鬧!陽壽未盡,自當速速歸體!”
我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大跳,驚醒過來,困難的努力地睜開眼睛,看到一室的慘白,燈光有些刺眼。我聽到有人在跑動,然后有個聲音在驚喜地叫:“醫生!醫生快來!他醒了!他醒過來了!……”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一部紅色的波蘭萊茲載著一家人風馳電掣。前方是至少兩公里筆直的路。不遠處是座旱橋,游玩的人象五顏六色的點在橋下跳躍。
車內彌漫著生氣。車輪碾過路旁的小草,濺起幾絲嫩的綠。
爸爸坐在駕駛室里。開車。聽歌。跟后坐的媽媽女兒搭搭訕。總之,很愜意。一個事業有成的男人在閑暇的時候同家人踏青,的確是減輕壓力的好方法。
風好大,吹得車窗外呼呼響。愜意的男人忽然發覺后視鏡沾了個紅紅的什么東西。他開窗,用抹布擦。安全是很重要的,絲毫馬虎不得。何況要過橋了。
與此同時,橋下野餐聊天放風箏彈吉他的人,都不約而同望向橋上。據目擊者陸柄國當時講,一部紅色的轎車,沖過旱橋護欄,以優美的弧線劃過天邊的朝霞,象頭巨大的鳥。
人們只認為這是一起交通事故,殘骸很快被拖走。燒得黑糊糊的一團尸體,讓法醫欲辨不能。
事故原因不明,作為一般交通事故,有關的照片和資料躺在交警隊的第178號卷宗里。無人問津。
直到有一天,一位老公安,無意查閱了在過旱橋一點八公里處幾乎同時發生的另起交通事故。經過精密推理,他把受害的一家與一個可憐的摩托車手聯系了起來。
第一宗交案——司機的死亡驚顫
爸爸哼著歌,愉快地擦拭著鏡子。
鏡子夸張地向四方擴展它的反射面。有人對鏡子存著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恐懼,為什么?天知道。理論上應偏向于有時候,人們會在鏡子里看到絕不應看見的東西。比如……
想到這里,爸爸不由得自嘲地笑笑——受黨教育這么多年了,世上是沒有馬列主義無神論解釋不了的東西的。
何況鏡子好好地在那,就象怯生生的女人,老實得很。
在爸爸擦干凈了鏡子,就要縮回手的時候,又有幾點紅色落下來。好象開玩笑一樣。爸爸有點不耐煩,然而下意識地,又伸過手擦拭。
0。01秒過后,玩笑開大了,一腔紅色的液體潑在鏡子上車身上爸爸來不及縮回的手上,0。02秒后,一個很象西瓜的圓球體重重地從外面砸在爸爸的腿上。泛著血紅的西瓜瓤。還在爸爸的腿上跳了兩下。
爸爸突然覺得從驚顫回到了虛幻的不真實,他很努力地想讓自己平靜下來。可他忽然覺得有股視線從最不可能的地方向他射過來。他的目光從前方不遠的旱橋移下來……方向盤正讓車輪筆直向前……時速表顯示著90公里每小時……
不正常的東西來源與他的雙腿之間,那個西瓜狀的圓球體。它的外層是摩托鋼盔。爸爸突然嘔吐起來,血壓急速升高,心臟四個腔不堪重負,然后這個男人身體靠著方向盤往右一歪,在這之前,心肌梗塞已讓他停止了呼吸。
因為他看見,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從鋼盔望向他,還在眨呀眨。
第二宗交案——摩托車手的死亡驚顫
趙福生很喜歡眼前的這部摩托。雖然牌子不響,但性能挺好的。
吹影首先要向大家伙簡略介紹趙福生這個人。趙福生正好處于一種超過37度血液就能沸騰的年齡階段。趙福生的第二任女朋友馮蘭說她就是喜歡她家福生那種虎虎的沖氣。馮蘭對兜風很感興趣,趙福生腦袋一發熱,就買了這部摩托滿足女友的虛榮心。
今天是馮蘭生日,趙福生記起前正在市區東和幾個哥們喝酒。馮蘭家住市西,也就是說,雖然現在是早上,但如果不快點是趕不上中午馮蘭的生日PARTY的。
所以趙福生用水抹了把臉就跨上了車。
路是很熟的,晨風吹在臉上,也很舒服。
可是趙福生又不舒服了。他前面的那部紅色的波蘭萊茲似乎在向他炫耀。趙福生試圖超過它,兩次都沒成功。
趙福生虎虎的沖氣于是就開始爆發了。“我日帽子,大爺還超不過你?”
前面是旱橋,趙福生決心在上橋之前運用嫻熟的技巧搞定波蘭萊茲。加油門,換檔,再換檔,
近了。
就在這時,趙福生忽然覺得脖子一癢。真的很癢。然后就好象是娘生下他時的那么痛——娘總喜歡齜牙咧嘴向他描述這種痛楚——因此趙福生認定這種痛比劇痛至少還要痛上一萬倍。
趙福生的目標逐漸靠近,摩托車漸漸和轎車并駕齊驅。
可趙福生現在覺得血液已經沸騰起來。捂不住,抑不下,血液真的從體內沖了出來,象一股股細細的噴泉。
趙福生看見了令他一生都要驚顫的東西。他看見了自己的脖子。然后是自己的身子。接著他的視角呈360度并傾斜著30度,以他的右耳為軸不斷變化著。考慮到地心引力,趙福生的這個頭不規則地跌進轎車內,從窗戶。
趙福生居然還看見了他的對手——一個中年的男人,極度扭曲他驚恐的面孔。趙福生瞪著他,嘟噥了一句,“我日帽子,怎么這么痛。”
趙福生的另外一部分,仍就架在摩托上,向未知的前方疾馳。
路是很熟的,晨風吹在身上,也很舒服。